男女主角分别是李巍李除く的其他类型小说《残砚泣墨录:李巍李除く番外笔趣阁》,由网络作家“道上道木”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夜思远”端砚放在了工作台上,单独用一个玻璃罩罩住。他没有立刻开始动手修复,而是打算先观察几天,感受一下它的“性情”。如林女士所言,这方砚台确实透着古怪。白天还好,只是那股若有若无的苦涩哀愁气息萦绕在工作台附近。但到了晚上,尤其是夜深人静之时,古迹斋里的氛围就变得有些压抑。李巍偶尔会听到角落里传来极其轻微的、如同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有时又像是有人在低低地叹息。更明显的变化发生在那方砚台本身。李巍确定,他没有记错,那道裂纹似乎真的在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蔓延,而砚堂中心那块深黯的墨渍区域,边缘也似乎模糊了一些,像是……正在向外扩散。与“幽冥鉴”那种直接、霸道的阴冷邪气不同,这方端砚散发出的“念”,更像是一种弥漫性的、具有感染力的负面情绪。李...
《残砚泣墨录:李巍李除く番外笔趣阁》精彩片段
夜思远”端砚放在了工作台上,单独用一个玻璃罩罩住。
他没有立刻开始动手修复,而是打算先观察几天,感受一下它的“性情”。
如林女士所言,这方砚台确实透着古怪。
白天还好,只是那股若有若无的苦涩哀愁气息萦绕在工作台附近。
但到了晚上,尤其是夜深人静之时,古迹斋里的氛围就变得有些压抑。
李巍偶尔会听到角落里传来极其轻微的、如同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有时又像是有人在低低地叹息。
更明显的变化发生在那方砚台本身。
李巍确定,他没有记错,那道裂纹似乎真的在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蔓延,而砚堂中心那块深黯的墨渍区域,边缘也似乎模糊了一些,像是……正在向外扩散。
与“幽冥鉴”那种直接、霸道的阴冷邪气不同,这方端砚散发出的“念”,更像是一种弥漫性的、具有感染力的负面情绪。
李巍发现自己最近也变得容易伤感,看一些悲情电影或读到伤感的诗句,情绪会久久不能平复,这在他以前是很少见的。
他也开始做梦。
梦境总是相似的场景:一个清冷的月夜,一间简陋的书房,窗外是萧瑟的秋风。
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儒衫的背影,伏在案前,就着一盏昏暗的油灯,手持毛笔,对着一方砚台,似乎在奋笔疾书。
李巍看不清他的脸,也看不清他写了什么,只能感受到一股浓得化不开的悲凉、愤懑和不甘,如同墨汁一般,浸透了整个梦境。
有时,那个背影会停下笔,发出长长的、压抑的叹息,那叹息声穿透梦境,直接响在李巍的耳边,让他从睡梦中惊醒,心头沉甸甸的。
“看来,光是观察不行,必须得想办法了。”
李巍揉了揉隐隐作痛的额角。
这砚台里的“执念”,比他想象的还要顽固和深沉。
他开始着手进行物理修复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清理。
他用特制的软毛刷和中性清洗液,小心地清洁砚台表面的污垢。
当清洗到砚堂那块深黯墨渍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无论他用什么清洗剂,那块墨渍都纹丝不动,反而颜色更加深沉,如同活物般吸附在石材上。
而且,清洗这里时,那股哀愁的气息和诱发的负面情绪也最为强烈。
<李巍皱起了眉头。
这墨渍,恐
复费用,珍而重之地将这方重获新生的家传古砚带走了。
送走林女士,李巍独自坐在店里,看着窗外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心中感慨万千。
修复“静夜思远”砚的过程,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次技艺上的挑战,更是一次深刻的心灵洗礼。
他前所未有地感受到,那些看似冰冷的古物之中,可能蕴藏着多么炽热、多么深沉的情感和故事。
他的修复工作,似乎也不再仅仅是为了恢复器物的外形,更是在尝试着去“倾听”它们的声音,去“疗愈”它们承载的创伤,无论是物理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傍晚时分,白老又溜达了过来,手里提着一小袋刚炒好的花生米。
“看你这气定神闲的样子,那方‘愁死人’的砚台,搞定了?”
白老笑呵呵地问。
李巍笑着点头,给白老沏上茶,将修复的过程和结果简单说了一下,隐去了自己用心血和墨的部分细节。
“嗯,以心为引,以敬为桥……路子走对了。”
白老捻着胡须,眼中露出赞许之色,“‘墨魅’虽非邪祟,但其执念若不能化解,久而久之,也可能因怨气积累而滋生变故。
你这次,算是做了一件功德事。”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
李巍说,“也是这方砚台,教会了我很多。”
“好好感悟吧。”
白老呷了口茶,“这长安城里的老物件,多着呢。
以后,有你忙的。
不过,切记,凡事量力而行,守住本心最重要。
有些东西,不是现在的你能碰的。”
李巍郑重点头。
他明白白老的意思。
这个城市隐藏的秘密,远比他接触到的要深邃得多。
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棂,洒在古迹斋那些沉静的古物上,给它们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
空气中,仿佛还残留着一丝淡淡的墨香,平和而悠远。
李巍知道,他的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故事一样,都还远未结束。
那些来自过去的低语,依旧在城市的角落里回响,等待着下一个倾听者。
而他,已经准备好,用他的手艺和一颗日渐敏锐的心,去继续触碰那些尘封的记忆。
7 完
、噩梦。”
白老说道,“那道裂纹的加深,墨渍的蔓延,恐怕也是‘墨魅’力量不稳、情绪‘外泄’的表现。”
“那……如何是好?”
李巍问,“这‘墨魅’能被驱散或消除吗?”
白老摇了摇头:“‘墨魅’不同于邪祟,它并非外来的侵扰,而是器物本身历史和情感的一部分。
强行驱散,等于抹去它的‘灵魂’,这方砚台也就彻底‘死’了,变成一块普通的石头。
而且,如此强大的执念,强行对抗,恐怕会引发更剧烈的反噬。”
他看着李巍:“唯一的办法,是‘解’。”
“解?”
“解铃还须系铃人。”
白老说,“要化解这股执念,必须找到它的‘心结’所在。
那位晚唐文人,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他最深的愁苦源自何处?
他临终前最放不下的又是什么?
只有找到这个‘结’,用合适的方式去‘疏导’、去‘满足’、去‘告慰’,才有可能让这股盘踞千年的执念得以释怀、消散。”
“这……我去哪里找一个千年之前文人的心结?”
李巍苦笑。
“线索,还在砚台本身。”
白老指了指照片上的四个字,“‘静夜思远’——这既是砚名,也可能是主人心境的写照。
‘远’,可以指远方,也可以指远大的抱负,或是……远去的人。
‘晚唐遗墨’的印款,也暗示了他的时代和身份。
你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去查阅晚唐的史料、文人笔记、诗词总集,看看能否找到与这方砚台风格、印款、名号相符的记载。”
白老顿了顿,补充道:“另外,‘解’的方式也很重要。
单纯的物理修复是不够的。
或许,你需要用一种……更贴近它‘心意’的方式来完成最后的修复。
比如,用承载着‘理解’与‘敬意’的墨,去填补那块顽固的墨渍;用蕴含着‘圆满’与‘安宁’的意念,去弥合那道裂纹。”
“这听起来……更像是某种仪式?”
李巍感觉这已经超出了修复的范畴。
“修复古物,有时候本就是一场与过往的对话,一场跨越时空的仪式。”
白老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用心去做,器物自会给你回应。
不过,务必小心,过度沉浸其中,也可能被其情绪同化,迷失自我。”
李巍再次向白老道谢。
他感觉自己肩上的
几首署名柳子言的诗。
这些诗果然如笔记所载,风格凄婉,意境愁苦,字里行间充满了怀才不遇的愤懑、报国无门的忧虑,以及对远方故乡或某个理想境界的深切思念。
其中一首《月夜书怀》尤其让李巍动容:“长安月冷照孤衾,思远空对砚石深。
十年翰墨十年尘,笔下龙蛇枉自吟。
家国飘摇风雨急,庙堂衮衮醉沉沉。
何时得遂凌云志?
不向人间觅知音!”
读着这首诗,李巍仿佛能看到那个月夜下的孤独背影,感受到他心中那份深沉的绝望和不甘。
他的“心结”是什么?
是无法施展的才华?
是动荡不安的家国?
还是……知音难觅的孤独?
李巍觉得,可能三者皆有,但最核心的,或许还是那份不被理解、不被赏识的孤独,以及才华抱负终究付诸东流的彻底绝望。
他将一生的精神寄托都倾注在了这方砚台和笔下的翰墨之中,最终,这执念也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不向人间觅知音……”李巍低声念着这句诗,心中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或许,“解”开这个心结的关键,并非去“满足”他生前的遗憾(这已无可能),而是给予他一份迟来的……“理解”和“共鸣”。
他需要完成的,不仅仅是物理的修复,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柳子言的在天之灵(或者说那段固化的执念):你的才华,我看到了;你的愁苦,我理解了;你的诗文,并非“枉自吟”,它穿越了千年,终究遇到了“知音”。
5 心血为引,墨韵相融明确了方向,李巍开始准备进行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修复步骤。
他没有选择常规的填补材料来修复那道裂纹和墨渍,而是决定遵循白老的提示和自己的感应,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进行。
首先,是“墨”。
他没有用市面上常见的墨汁,而是取出了自己珍藏的一块明代古墨——“曹素功制‘紫玉光’”。
这种古墨质地细腻,色泽沉厚,本身就蕴含着浓厚的历史文气。
但他觉得还不够。
他想起了《长安闲谭录》中那句“墨尽则以心血和之”。
他犹豫了很久,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净了手,用消过毒的银针,轻轻刺破了自己的指尖,挤出几滴鲜红的血珠
怕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渗透,而是那股“执念”凝聚的显化。
接着是处理裂纹。
这需要极高的技巧。
他选择了传统的“锔钉”工艺,用细小的金属钉将裂缝固定。
但在钻孔和嵌入锔钉的过程中,他明显感觉到一股无形的阻力,仿佛砚台本身在“抗拒”被修复。
每嵌入一枚锔钉,那股哀愁的气息就会波动一次,梦中那个背影的叹息声也似乎更加清晰。
物理修复进行得异常艰难,进度缓慢。
李巍知道,不解决“执念”的根源,后续的打磨、填补都无法顺利进行。
他再次想到了白老。
或许,白老那里有关于这种“文房执念”的说法和应对之策。
3 无事清谈,墨魅心结依旧是城墙根下的“无事”茶馆,依旧是那棵老槐树,依旧是悠闲品茗的白老。
李巍将“静夜思远”砚的情况和自己的遭遇详细说了一遍,并拿出拍下的砚台照片给白老看。
白老眯着眼,仔细看了看照片,又听完李巍的叙述,沉吟了片刻。
“‘静夜思远,晚唐遗墨’……”白老缓缓道,“晚唐啊……那是个英雄末路、美人迟暮的时代。
多少才子佳人,空有凌云之志,却生不逢时,最终只能在历史的尘埃里留下一声叹息。”
他指着照片上砚堂的墨渍:“这方端砚,恐怕是沾染了‘墨魅’。”
“墨魅?”
李巍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嗯。”
白老解释道,“不同于山精鬼怪、凶穴邪祟,‘墨魅’并非实体,而是一种由极其强烈的精神意念,尤其是文人的才情、愁绪、怨念、执着,长期浸染文房器物(特别是笔墨纸砚)而凝聚形成的‘念灵’。
它没有自主意识,更像是一段被固化的、不断重复播放的情绪和记忆。”
“这方砚台的原主人,那位晚唐文人,恐怕是将毕生的才华与不甘、愁苦与思念,都倾注在了这方伴随他无数个不眠之夜的砚台之中。
他死后,这股强大的执念没有消散,反而与砚台本身、与他最后留下的墨迹融为一体,形成了‘墨魅’。”
“这‘墨魅’本身并无害人之心,但它蕴含的负面情绪太过强大,如同一个情绪漩涡。
靠近它的人,会被动地卷入其中,心神受到影响,变得消沉、悲观,甚至被其残存的记忆碎片干扰,产生幻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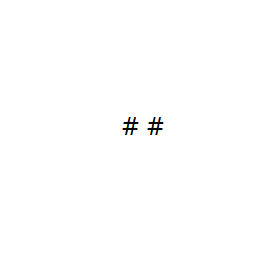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