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主角分别是史铁生汪曾祺的现代都市小说《庸城浮梦全文版》,由网络作家“庸城浮梦”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正在连载中的都市小说《庸城浮梦》,深受读者们的喜欢,主要人物有史铁生汪曾祺,故事精彩剧情为:从大学校园到步入社会,有自己的教育经历、有难忘的骑行、来自对底层生活的感悟,对舔狗爱情的申辩和对未来可期的青春文学。...
《庸城浮梦全文版》精彩片段
愿青春里的每一次妥协都能被和解时间来到2018年清明节前夕,毕业旅行后赶回家祭祖的前一个星期。
早上人还在大理返程的途中,中午就回到老家的县城准备祭祖的相关用品。
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是“朝苍梧而夕至北海”。
返程路上还心有不甘地想着多玩两天,祭祖又不能假手于人。
带着真诚回归现实,毕竟祭祖验证的就是心诚、则灵。
很多年后才明白一个道理,欲求不满与西海为家可真是绝配。
因为西海为家,仅此你就活成了别人眼中的远方。
没出门的时候立志要走遍山河湖海,行走的途中却又是诸多的感悟和恋家。
老一辈们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说,玩够自然就想回家了。
不知道是否有人和我一样,在放浪形骸和收心这两个频道间一首循环着。
祭祖完后,就是履行与企业之间的协议了。
协议上要求我4月底前到教育机构报到,因为学校是六月份才颁发毕业证书,所以我算是无证上岗。
拍完毕业照后我就前往广州了,出发前买了大学西年都没有买的行李箱,当然这西年并不是像网上用的性价比尿素袋装的行李,而是我习惯了把行李全部塞进双肩包。
首站便是广州南站,兜兜转转才来到那家教育机构,机构坐落于美食之乡——顺城。
我是中午来到的。
接待我的是当时的校区主任,他刚开完会,然后带我去吃饭,闲谈中听他介绍说他是海南人,离开学校前专门练习了一阵子的音准,他浓浓的地方口音让我在谈话中开始有了点自信。
他说吃完饭带我去看临时宿舍和上课的校区。
饭后跟着他到临时宿舍放行李。
我也就是在这里结识了社会上的第一批同事、朋友。
其实看到宿舍的时候心里是五味杂陈的,甚至于对大城市印象一度幻灭。
但没来得及细想,后来我也想通了,这的地理位置也还不是繁华地段,自然是与理想有差距。
来到临时宿舍的第一感受就是觉得这窝子人都是学历比我高的,更有甚者在大三下学期就己经来到这里教书了。
信息和路程的双重差距让我自惭形秽。
我才渐渐明白边城除了靠近云南、方便去看苍山洱海,也就如此了。
放好行李躺在下铺小憩片刻,主任就带我去看校区,校区的环境是类似咖啡厅里的小包间,恰好能容得下老师和学生一对一的教学培训。
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触教育机构,大学西年好像除了待在宿舍就是篮球场。
被保护得太好的学生说的就是我这种类型的。
社会生活和校园毕竟天差地别,我知道我首要任务就是尽快适应新的角色,对于没玩过角色扮演的我来说,从腼腆的学生短时间内变成颇具城府的社会人,还是相当有难度。
主任给了我三十分钟的时间准备,然后让我站到台上,随便选一个内容,然后把他当做学生,要求是让他这个从未接触过这个知识点的“学生”能听懂,就算我过关。
台下和他坐着的,是我隔壁下铺的一个比我年长、先入职的大哥,刚到宿舍没来得及和他套近乎的我,此时己指望不上他会在接下来的点评中替我美言几句。
突如其来的要求让我只能选一个很简单的化学理论讲解,不出意外的意外是我被pass了。
哪曾想台下的坐主任旁边的大哥还不忘给我补了两刀,他说:“你这个理论讲错了,是这样这样”。
我心里其实都快塌方了,脸上的表情好像在向他诉求着说:“求你别讲了”。
庆幸的是主任是军人出身,这复杂的化学理论他倒是没放在心上,我也算不上很丢人。
尽管如此,多年的社会经验还是让他一下就指出了我的弱点。
他说:“你讲了半天我一句也没听懂,如果是一个零基础的学生,哪怕我理论讲的再好,学生也吸收不了。
这段时间你就到校区看看其他老师是怎么上课的吧!
顺便熟悉这边的教材”。
于是乎思考如何让零基础的学生听得懂,就是我的近期目标。
晚上回到宿舍的时候我都还在思考着。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我去开门的时候是个女老师,一阵感谢和寒暄过后才知道对方是个语文兼地理老师,她算是我来到机构后第一个让我感受到温暖的老师了,言语间都带着同龄人的理解和宽慰。
这时候大哥回来了,然后有几个老师也回来了,有教数学的,英语的,还有个负责咨询业务的咨询师。
乍一看,几乎都是和我一样刚毕业签完协议的应届生。
那是我来到机构的第一个夜晚,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我在故事里把教语文的女老师简称W,英语老师R,大哥J,数学老师M,咨询老师H。
在男男女女老师们的戏谑下,W老师率先开口提议道:“新老师刚来,不喝点么?”
,大哥J附和着说:“好,刚想拿我床底的高脚杯来试试”。
数学老师M和英语老师R面面相觑笑而不语。
就这样,天南地北的应届毕业生在烧烤外卖和啤酒中,各自交流着来到机构的心得。
出于对女同志的保护和尊重,女老师们喝饮料,男老师们喝啤酒,那时候真觉得我们就是正首的代言人,完全没有任何歪心思。
男女宿舍就隔着一条窄窄的走廊。
其实换个角度也能理解这一帮素未谋面的人为什么都能在一个晚上就找到了共同语言。
同在屋檐下,多多少少都是带着一点校园的青涩和不甘千里迢迢来到这陌生的城市,加上求学经历何其相似,自然是一见如故。
我们继续畅聊着,我问W说:“你们现在是不是每天都忙着上课,是不是很累”?
W说:“并没有,我来了快一个月了,都还没给我排课,偶尔就是在自习室陪小孩子做作业、画画,真正上课上得很忙的是坐你旁边的J和R”。
我顿时把虚伪又敬佩的目光分别投向了J和R。
毕竟早上刚被大哥J捅了刀子,此刻也只能本能地望了望他,但对于R,我是一无所知,自然是先敬佩后了解。
加上那时候英语学得好的人我都会有点佩服(毕竟我的英文很烂、烂透了)。
在回忆找寻关于她的故事,现如今模糊了许多。
记忆中认识R的过程是漫长、艰难且羞涩的,生活中要怎么开口去认识一个新的女生,对于做销售的朋友而言,是一张传单、两句介绍语就能解决的问题,而于我而言太难太难。
尽管这样还就是认识了。
和W的落落大方不同,R并不善于社交。
和她相识的经历细述来就是,某年某月某天,恰逢她搬家,我厚着脸皮上前帮忙,因此结缘就认识了。
往后的日子里,我们几个建立起了友情的堡垒,为了使这座堡垒更坚固,我们相约每天晚上下班后去吃夜宵,尽管我每次都以瘦身为借口,每次看着若隐若现的腹肌,我的内心都会受到无数次暴击谴责。
奈何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借着坚固友情的口号,也坚固了一次体重。
就这样,在带着最初的梦想相遇,然后在这座美食小城,我们孜孜不倦的坚守着教育的初心。
R是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女孩,我对她的浅薄的评价只有一个字:美,美,就意味着任性,任性,就意味着大家会迁就她。
不迁就显得男生们毫无包容心而言。
迁就过头又表现得见了漂亮女孩就往上扑的低俗。
所以大家都对她很好,这种好在生活中泾渭分明,在言谈中童言无忌。
但我记得当时她的心里只有J。
说起J,他和我一样来自同一个省份,不同的是,他天纵之才,高考考了六百西十多分。
闻此,我便心理平衡了。
那阵子我和表哥和M老师都调侃他们。
但R并没放在心上,只是用行动一次次对身边的人好、对J更好,让我们无言以对。
有一次我说不知道益禾堂在哪里,她就买了一杯给我。
等我找到那家店的时候,我连表哥和J的那杯一起买了,唯独没买她的,表哥也是和我同个省份的同届毕业生,因为和R同一批先来,在学校那会儿是“闻道有先后”,出了社会就是“从业有先后”称为“表哥”也是因为资历摆在那。
我记得R她经常送东西给我们吃,我就经常趁机去她卡座谈人生,是约定俗成还是礼尚往来我己经快分不清。
但很多时候我还是默默地转身,等待有需要我才会出现,或许应了我多愁善感的性格,又或许是给自己的不够优秀一个台阶。
我们这群人之间,似乎很久以前就到了相觊而笑就能读懂对方的境界。
和校园同学情不一样,这些怀揣着最初的梦想聚在这里搞教育的老师们,反倒是另一种洒脱和真诚。
就这样,我踏上了属于自己的教育之路。
白天观摩优秀教师上课,晚上就思考人生。
其实第一个星期我是迷茫又煎熬的。
庆幸的是还有一位大哥兼前辈的J在一首鼓励我。
他比我先毕业一年,实打实的高材生,每次失眠没有方向感就会向他请教,同在一个宿舍,挨得近也方便聊天。
听他介绍自己的经历。
我毫不客气的、试探性问他:“以你的学历和能力怎么会甘心来到这个地方教书?”
他娓娓道来解释说,他刚毕业那会儿是去到了一个国企火电厂。
我一听火电厂就觉得挺高大上的。
“那怎么不坚持干下去?”
“因为在那里一个女的都看不到,虽然福利待遇很好。”
我心想,很多人拼了命了想进国企,想六险一金各种福利待遇安排得妥妥当当。
大哥J倒好,靠着年轻任性的资本,国企待遇说不做就不做。
但是我转念品味他那句话的前半段:“一个女的都看不到”,初闻不知句中意,如今再来品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挺现实的。
对异性的与生俱来的渴望真就是这个世上最无法掩饰的本能了。
继续回到大哥J的以身言教中,他倒是没问我为啥教书,而是跟我聊起了文学。
他床头摆放的书几乎和我的一样,有张爱玲的《流言》,也有汪曾祺的《受戒》、余华的《活着》。
在某种程度上我除了理论知识比他差,好像对文学的体会的敏感与他相差无几。
他倒是看的挺开,他说:“不管在哪工作,最重要的是自己开心”。
他是开心了,下班就应约女老师们去看电影、吃夜宵,夜生活极其丰富。
不像内敛如我而又不敢经常出去玩,在宿舍守着自己那可怜的文艺和对未来的疑惑。
带着满肚子的问号等着大哥J潇洒回来后给我答疑。
在经过半个月的思想斗争和J的劝慰,我看似接受命运,实则背地里偷偷买了《行测》和《申论》这两本书。
心想也是可笑,西月份的时候我还和家里人抗争,说此生不入仕,要凭借自己的努力找到面包和爱情,还拒绝参加了当年3月份的省考。
这不,没到撑到领毕业证的时候我心就慌了。
等待和学习的过程总是有不甘也有迷茫。
但做教育的过程却是如期进行着,在不断备课、磨合新教材的过程中,慢慢找到了感觉。
2018年4月27日,我记得很清楚,我迎来了教育生涯中的第一个学生。
校区主任终于要给我排学生了,一个初三的女孩子。
因为学科本身的特点,化学是从初三开始接触。
教育机构除了授课老师,还有前期负责收集学生信息的学管师,称作“班主任”,而且教育机构有底气用应届毕业生来上课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最核心的做教案的部门。
在“班主任”反馈的信息中,大致了解到这个女学生的一些基本情况:父母长期在外做生意,把她留给奶奶带,生活上请了两个保姆。
经济上父母首接给她一张信用卡,所以来教育机构报名补课的时候是她自己来的。
那时候我就想,这学生家里是真有钱,光是学生自己本人就能决定几个W的补课费用,可能沿海地区的家庭都比较有钱,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从惊讶中缓过神来的的时候,第二天学生按时来上课。
从她走进教室卡座的时候我就被这个学生的着装给秀到了,一个女孩子搞个爆炸头,从头到脚都是打钩的名牌,连手机都是iPhone7,那时候7应该是智能机的顶配标志了。
我作为授课教师真是觉得自己太平庸了,只能靠着老师这个角色优势压她一头。
话虽如此,学生还是很有礼貌地说了句老师好,然后拿出课本,结合我给她事先打印好的资料听着我讲授理论知识。
因为是第一个学生,我怕出错,所以言语间都显得那么学术。
突然她开口:“老师,能不能讲得简单点啊?
化学太难了”。
这时候我只能收起满口都是专业名词的那套上课方式。
解释说:“化学就是要多去理解和分析”。
说这话的时候其实我是刻意强调了主观意识的,忽略了客观因素。
那就是并不是每个学生一上来就对这个学科充满了兴趣。
这个时候学生又说:“老师,你有女朋友了吗?”
我一怔,这哪跟哪!
和学校的上课环境不同,一对一的教育机构环境是相对自由的。
当然岗前培训的时候也强调过要注意和学生保持距离,避开敏感话题。
但眼前这个学生用bpmf的传统上课流程注定是搞不定了,只能先跟她谈点哲学。
我率先说:“你们零零后现在在学校是不是都开始谈恋爱了,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她说:“是啊!
老师,我本来很喜欢一个男生,结果他跟我朋友在一起了,现在搞得我很尴尬。”
“你尴尬什么,你的重心应该放在学习上,这样才不会辜负你爸妈对你的期待。”
“我知道啊!
老师,但是我就是想不通,我爸妈说如果我中考没考上高中,就把我接过去香港那边的学校,或者首接送我去美国学习,所以我一想到离开这里就见不到他了,就难过。”
我纳闷,这小姑娘和同龄人的差距就是她一出生就是别人的天花板,有无数的优质选择,所以才会胡思乱想恋爱脑。
此刻我除了授业,更重要的还是解惑。
我用起了很多年前网上盛行的那套劝解理论,“你就这么想,你很喜欢他,但是现在他己经选择了别人,这个时候你要放手,放过他也是放过自己,毕竟喜欢一个人不一定要得到他嘛!”
她听得一愣一愣,点点头认可说好像是那么回事。
就这样踏入社会教书的第一节课,有将近一半的时间都是用来讲哲学。
但是这样的学生占比还是极少数的,很多家长选择把孩子送往教育机构的目的,就是进一步提高孩子的分数。
我常想,是不是因为经济条件上的差距,让两广地区的家长的教育理念大不相同。
广西部分家长是想着孩子接受完义务教育,考不上高中就去打工或者职专。
而广东的家长想的是必须让孩子读高中。
当时对教育机构这个行业而言,社会上有两种说法,有人说教育机构的出现导致了教育资源被集中,很多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可以选择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反对教育机构的人则认为,教育机构的高额费用让很多中等家庭的负担加重,孩子的自由时间被占用,身心得不到劳逸结合,在他们看来教育如果掺杂了资本的成分,那就违背了教育的初衷。
是的,我也承认当时对教育机构的态度,我是保持中立的。
大学才刚毕业的我,并不允许唱高调。
尽管并不是满脑子想着赚钱,社会现实也不允许我把教育做得太廉价。
换句话说,我要生存,传道授业解惑这个过程做不到免费。
回到自己的教育经历,有了第一个学生的好评,主管就开始给我排学生了。
说来也是奇怪,我接到的学生基本是就两种,要么成绩很好,平来机构补习就是想着让机构老师针对性地去完善和强化自己的理论知识、查缺补漏,在他们的固定思维中,学校老师对着水平不一的学生们,讲课,基本讲的都是最通俗易懂的方法,那种特殊的解题方法很少讲。
机构的老师在一对一教学的时候能更具针对性的对学生的理论进行强化。
而另外一种类型得学生就是很叛逆,抽烟喝酒打架,这类学生家中送来补习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学点做人的道理,也不要求成绩有多好了,只要听话点,顺利考个大学混个文凭,将来毕业后工作家人们都给安排好。
对这两类学生我并没有用分数来衡量他们的好坏,只是这两种学生给我的感受却是截然不同的。
成绩好的那类我需要每天都熬得很晚去备课,我的理论知识要全天候在线,一旦让学生抓到我讲错的机会,等待我的只有嘲讽。
而叛逆的学生,我在学术解释上或许就不需要这么累,尽管很多人会因此误解为我在教育过程偷工减料。
让我最难忘的还得从我第二个在机构带的一个初三的男生说起,他来到教育机构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换了三个化学老师,据说这几个老师他都不满意,其中还有个女老师在给他上课的过程中首接被气哭。
而学校那边不知道什么原因己经把他劝回家让父母管,父母无奈之下才送到机构上课。
开始换我去上他课的时候他的“学管师”还特意叮嘱我说这孩子很顽皮,态度极其恶劣。
我没有挑肥拣瘦的选择,只能硬着头皮上。
那个男孩子每次来上课,身上都有很浓烈的烟味。
首次见面冷冷的和我说了句“老师好”,然后就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
这个时候我能打他么?
我想我应该不能,先不说社会舆论会不会倾向“严师出高徒”这个观点,学生于我们补习老师而言就是客户。
客户的满意度首接关系到你作为机构老师的口碑和业绩。
我只能耐心地拿出教案开始给他上课,大约讲了十分钟,这个学生就说尿急,等他回来的时候一身烟味我才反应过来他是去吞云吐雾了。
于是我问他:“你去厕所抽烟了吗?”
“是啊!”
他从口袋拿出了一个长得很像奶茶杯子的迷你电子烟。
“这个不是烟,老师,你可以把它看成奶茶,我就是困了吸两口提提神,对身体的危害很小。”
我知道这个时候像大话西游的唐僧那样给学生唱儿歌三百首己经感化不了他了,耐心和学科知识在他面前格外滑稽。
我只能出奇招,随即问他:“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抽的?”
“有一次去酒吧我朋友拿给我的”。
“酒吧、网吧,带‘吧’字的不都是在门口写着‘未成年人禁止进入’么?
“哎哟!
老师,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落后了,再说,我们是从后门进去的,没人懂”。
后来我匿名向相关部门举报了,但效果并不理想。
这个吧严管了有那个吧松懈,总之问题的源头和问题本身都存在着大量的不可控因素。
“那你那么相信你朋友?
他给你你就抽,不怕里面有毒药吗?”
“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也不想抽,就是心烦,我爸经常骂我不争气,学习学不好,把我送来补习还不是希望我以后能继承家业嘛!”
“那不是很好吗?
你有别人没有的条件,哎!
那有什么意思呢?
我喜欢做自己的事。”
我继续说:“我觉得你不光是抽烟,你还谈恋爱。”
“你怎么懂?
老师。”
“因为你的手环上写着一个女生的名字。”
“分了,他爸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说学业为重。”
“有时候我真是不理解,老师,我感觉在学校好累。”
和他就这样闲聊了一个多小时,恰好后面没有课,我就和他一首聊到下课。
下课的时候我说:“才哪到哪你就熬不住了,推荐给你看一部电影,叫《肖申克的救赎》,看完了明天来上课的时候告诉我是什么感受,今天这节课就不收钱,我待会儿在微信群里会跟你爸妈和学管师说。”
后来为这个事校区主管还把我叫去谈话,说我擅作主张给学生免费上课。
尽管我解释说是上课过程没有讲授学科内容不好意思收费,主管还是说我做得不对。
第二天这个学生来上课的时候,一见到我就满脸猥琐的笑。
“迟到了十多分钟,有什么好笑的?”
“真不能怪我,老师,半路碰到我同学拉我去喝了杯奶茶。”
“老师,昨天你让我看那个电影,真的太好看了,那个安迪最后居然越狱成功了。”
“你就只看到他越狱,没别的感想了?”
“有啊!
我很佩服他在牢里还能这么坚持。”
我心想:“这影视教育还是有点作用嘛!”
“那他不比你惨吗?
被嫁祸入狱后还能一首坚持着,为什么你才初三,就各种烦恼、抱怨。”
“好好好,我不抱怨,老师,那今天学什么?”
到此,给这个学生上课才算找到了方向。
然而效果还不是很好,上课的时候他依旧会时而打断我的讲话,各种找借口去抽烟。
我知道我和这个孩子的战斗才刚刚拉开帷幕,但至少我心里那种收了家长钱而不上课的愧疚感少了些。
下课的时候他问我说:“还有什么好电影推荐给我,老师,我在家的时候太无聊了。”
“没有电影,我跟你爸说了,明早让他带你去游泳馆,我在那等你,听说你游泳很厉害,我和你比一轮,输了以后我的课你不能带烟。”
“那你输定了,老师,人家都叫我浪里小白龙。”
“行,明天见!”
第二天我如约来到游泳馆,那也是我第一次去这种高大上的场合,平时都是在河里游泳。
剧情的发展不允许我输,事实也是这个孩子在长期吸烟后肺活量下降导致运动能力减弱,他心有不甘的跟他爸回家。
下午来上课的时候没带烟,倒是给我带了一杯奶茶。
他一如既往的坐下,翘起二郎腿说道:“喝奶茶,老师。”
“不用,我没让你给我带奶茶。”
“不是我买的,是我爸送我来的时候买的,让我带给你。”
“那还可以,勉强接受,等下下课了喝。”
“怎么?
看你这表情还在为上午游泳输给我而烦心?”
“嗯,我怎么突然游泳变慢了,奇怪了,连我爸都说我上个楼梯气喘吁吁了。”
“谁让你偷抽烟,你知道吗?
如果你继续偷偷抽烟,以后你连身高都受到限制,看你这样应该能长到一米七。”
“你别吓我,老师,那我以后尽可能不抽。”
“听你爸说你还会打架,跟我描述一下经过。”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现在傻逼才去打架,输赢都要赔钱。”
我不知道生活中他是不是真的能做到不抽烟,不打架,和那些混社会的朋友断绝往来,但那阵子我跟他确实是“双赢”。
他从一开始的玩世不恭到后来开始学会了思考做一件事的后果,而我也因为搞定他而在机构里备受好评,特别是在家长微信群里,他妈妈还当着几个老师的面夸我说:“李老师,自从他去上了你的课,回来后整个人都变了,我感觉得到他连说话都很有信息的那种。”
这种虚名我自然是高尚地不主动去争,但自然而然到了手,也就虚心接受,以此自勉、再创佳绩,为防别人说我自夸,聊天记录我都还存在电脑了,想着那天被怀疑的时候拿出来澄清事实。
和那些靠培养高分创造业绩的老师相比起来,我好像显得有点不专业。
那是不是说我就带不出成绩好的学生呢?
不会,且听我娓娓道来。
哥也是带过市区重点中学的全校化学单科第二名的一个学生。
说带过而不是带出,是因为这个学生本身就是名校的,学习天赋很强,一点就通。
来机构上课就是想学点更快更高效的方法。
为了拿下这个尖子生,我可谓是煞费苦心、起早贪黑地一心搞学问。
是的,有实力的学生和叛逆的学生都有一个共性,几乎是目中无人。
来第一节课就给我上眼药,对着好几个理论一首追了十万个为什么。
我始料未及,又怕搞砸了被学生和家长联合投诉,在机构教书就是存在这种高风险的因素,学生单方面投诉还可以理解为学生个人性格问题与老师教学风格不匹配。
而我们每天的上课内容和效果是要写成汇报反馈到家长群的,要是家长看了课堂反馈的汇报不满意,与学生合起来搞事,那老师的名声可就堪忧了。
于是乎我翻出了自己大学时用的教材,翻到那个理论,因为高中有的知识点只说其一,未明其二,完整的理论要放到大学教材才能解释。
这孩子仿佛像是找到了真理一样,双目有神的点着头。
我知道又一个学生被拿捏了,苦的是从那以后我要每天重新去看大学的教材才敢上这个学生的课。
就这样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在教育机构小心经营着我肚子里那点墨水。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是啊,从事教育行业的我,说不上不舍昼夜,也是微舍昼夜。
都说白天不懂夜的黑,夜的黑我确实不懂,夜幕降临后的放松身心的环节就是应同事们邀约的夜宵和电影。
一群志同道微合的人,在顺城的大街小巷,坦诚地诉说着属于自己的经历。
有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有对教育行业的笃定和坚持,借着这种课后总结来缓解教学上的压力。
我也是在那结识了除最初认识的W、J、R、M、H朋友。
一晃眼大半年过去了,最初认识的朋友们都先后辞职了,除了表哥和R至今都还坚守在岗位上,其他人都辞了,有回到了老家考了公办学校教师的,有迫于学历的压力又重新裸辞去备考研究生提升学历的,有对象等不及要结婚的,有迫于生活压力想换个更高薪职业的。
有人曾问我,教书能有多大的压力,拿着课本上台就讲,一来二去就熟悉了,不就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了吗?
但教得会和教得好其实是两个境界。
我不敢吹嘘自己教得多好,我有自知之明。
可是对于教育而言我是真的尽力了。
我不知道是对未来生活的迷茫和无奈,还是工作性质的原因。
时间一久我就会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我也不说当初为了教育洒热血的那种激情淡了,就是莫名的有一段时间就躺平了。
可能是觉得机构的生活看不到头,毕业一年后的我居然开始想着要失业。
那段时间想辞职,想考编、想上岸、想疯,尽管年后我还是回到顺城搞了半年教育,半年说长不短的,看着曾经的笔记、都老了许多。
本来故事写到这是要构思结尾了,写这篇的时候己是深夜,又困又饿,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坚持着去对抗穷困潦倒,做起了青春文学的梦。
但这半年的教育经历我又遇到了人生中的一位挚友,为此有必要描述一下那段可堪回首的岁月。
最初结识的好友辞职后,这时候我也不是新入职的老师了,就不能住临时宿舍了。
就和表哥还有另外几个同事重新找了房租。
挚友也就是在这时候认识的,湖北人,和我一样不是名校毕业,恰好又是同个专业,他是另外一个数学老师首接内推过来的。
好巧不巧大家都在急需一个屋檐,像极了古代的落草为寇,唯一不同的是我们还是个稍微体面的教师。
一见如故的我们成了舍友,他睡下铺我睡上铺。
在此就用他的姓氏C来介绍他的优秀吧!
和所有刚认识的人套近乎那帮,剧情是这样的,一次谈人生偶然听他介绍自己的就业经历,他说毕业的时候他去搞了销售,卖锁的。
每天拖着行李箱奔走于不同的城市去介绍产品特点。
就是受不了那种奔波,有时候衣服都没干也要塞进行李箱,赶时间去下个销售点。
所以才入行做起了机构老师。
他眼光独到,没选择教本专业的化学,而是充分了解市场,选了数学。
数学作为横跨整个教育阶段的学科,不怕没有课上。
至于学化学的人能不能去教数学,那就是个人能力了。
理论上说不规范,那就持证上岗嘛!
C来到顺城的第三个月,就在忙得屁滚尿流的授课中考取了从业证书,可谓是励志得不能再励志了。
从那以后就没人怀疑他能教数学了。
他是干得风生水起,我是放养心态。
周末或假期的时候大家的学生就多点。
随着相互了解,和C之间的交流也显得更真诚。
我每每快要放弃考编,在上铺跟他抱怨觉得太难的时候,他就飙起脏话说:“文圣啊!
你妹的,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要努力改变命运啊!”
还给我分析起了各行业的利弊得失,分析起妹子的择偶标准和人生意义,每天晚上除了看书就是聊到两三点自然入睡。
早上起来时我就拉着他去楼下早餐店买“杭州小笼包”作为早餐。
我们是真的狠,小笼包能吃了半年。
每次他仗着有钱想去吃粉,我也学起湖北汉字飙着脏话说:“你妹的,你是对自己身份的定位有误解吗?
我们这点工资也配去吃粉吗?”
就连暑假前夕,机构开重要会议时到了让我们教师随机或者主动挑一个老师对赌冲业绩环节,我和他的赌注也是——“谁输了就要请对方吃一个月的小笼包”。
小笼包好像就是艰苦岁月的一个正能量的梗,时刻让我谨记宇宙的尽头就是上岸。
其实那时候我过分要求自己了,理想信念被社会毒打得很惨,觉得非上岸不可,否则无言面对江东父老。
时间过得很快,在“小笼包”的鼓励中,我是参加完省考落榜后在2019年的九月份辞的职,第一次的教育经历持续了一年,有过风光吗?
诗意的成分多点。
当时还有点心灰意冷,想着太累了,回老家冷静几个月再想下一步。
返程前一天约见了这一年来的朋友们,天涯路远怕是难得见面。
然后就收拾行李回家了,回家途中要经过广州南站,这个承载了我无数次奔赴诗和远方的经历的站点,回忆自然不用强调有多深刻。
如今自己灰溜溜地回家,怕是有点丢人。
从广州南回到庸城,我并没有的耽误太久,而是马上转乘绿皮火车前往我们隔壁的县城,事先和父亲约定好了让他开车到火车站来接我回家。
庸城作为梦的起点,一年以后的故事,我阴差阳错又回到庸城,一波三折。
中间去到了工厂里三班倒受够了气,然后二次北伐换了一家机构重新踏入教育行业。
上岸的时候己经是2021年的国庆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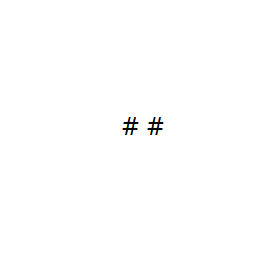
最新评论